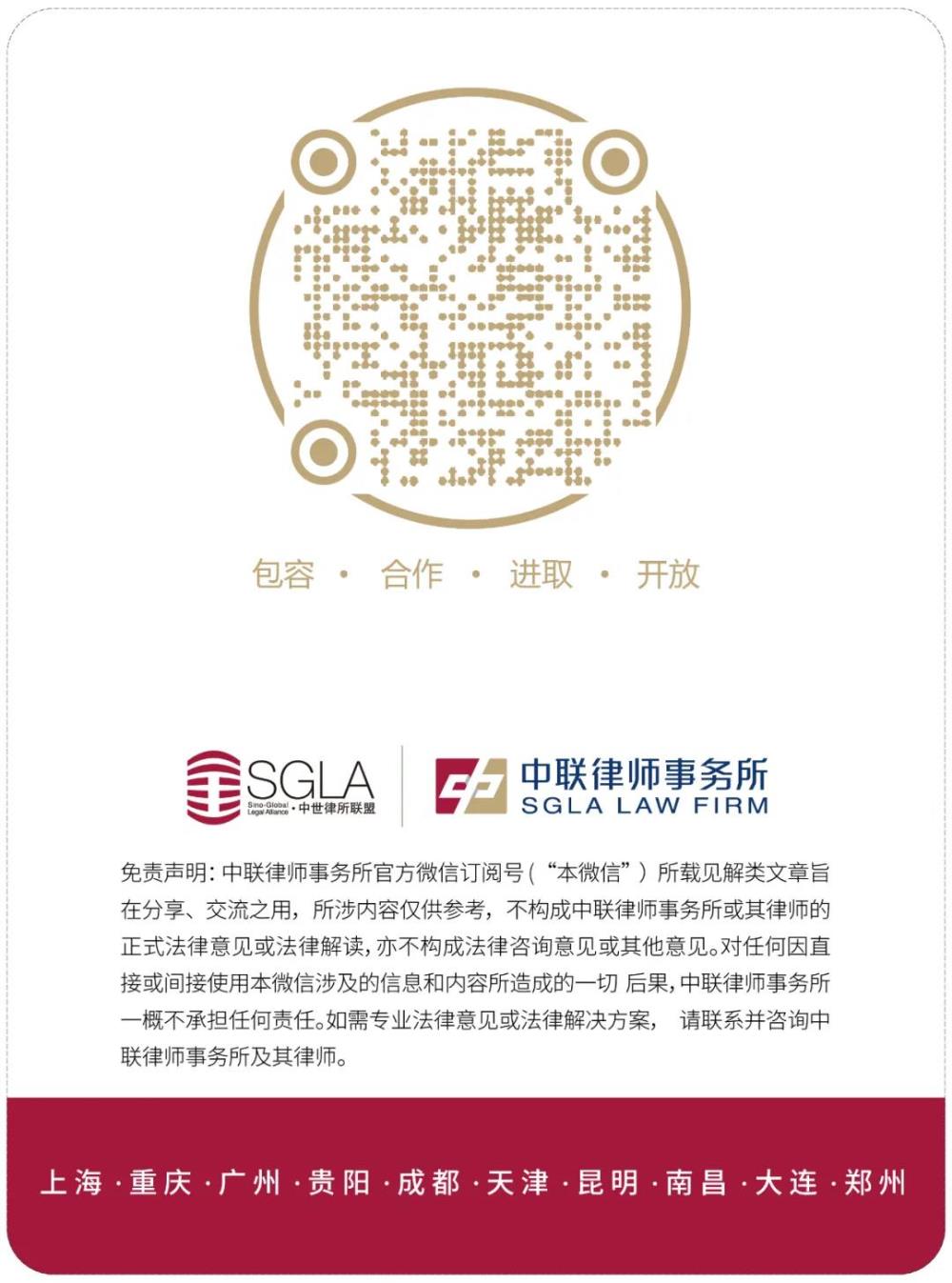摘要
关于近期司法裁判对“交易型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名租实贷”的判断观点,应首先注意,车辆是否办理转移登记不应成为判断所有权转移以及业务性质的决定因素。对该类业务的性质判断核心,应在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中购买环节的支付对象、不恰当的抵押登记、租赁物是否实际转移、是否办理转移登记等可能成为影响司法机关判断的综合性因素。“交易型售后回租”在近期可能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态度,相关企业在经营中应注意法律风险的防范。
一、近期司法裁判对“交易型售后回租”融资租赁性质的否定观点
(一)汽车融资租赁中的“交易型售后回租”模式
在汽车融资租赁行业的实践中,多采取“交易型售后回租”的经营方式:即车辆买受人在购买车辆的过程中,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由融资租赁公司向销售方支付价款。在车辆买受人获得车辆所有权后,向融资租赁公司转让车辆所有权,然后回租车辆。在该过程中,通常不办理车辆所有权的转移登记,有时还会存在对该车辆以融资租赁公司为抵押权人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
(二)“奔驰融资租赁案”中法院的否定性观点
“交易型售后回租”未办理转移登记以及将款项直接支付于销售方的形式,与典型的“售后回租型”融资租赁的交易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在最近的司法实践中也受到了的否定性评价。
1.“奔驰融资租赁案”的基本事实
在近期受到广泛关注的“奔驰融资租赁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2民终3147号民事判决书)中,毛某某(承租人)因购买车辆与奔驰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约定:奔驰租赁公司向毛某某购买已从卖方处购买的车辆并将其回租给毛某某使用,毛某某同意向奔驰租赁公司转让车辆的所有权;毛某某向卖方支付约定的预付款后,奔驰租赁公司将购买价款转入卖方指定账户;合同项下毛某某向奔驰租赁公司支付的全部还款金额由融资成本总额和融资费用总额构成。同时,奔驰租赁公司还与毛某某签订了《抵押合同》,约定:抵押物是《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项下得到融资的车辆。毛某某购买涉案车辆后取得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登记在其名下。随后该车辆进行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奔驰租赁公司。后毛某某未支付还款,遂成诉。
2.法院观点:“名租实贷”
该案一审法院认为:车辆系需要登记的不动产(注:一审判决原文),实际所有权并未转移。奔驰租赁公司将购买其余价款转入卖方指定账户,并将承租物设定了抵押权,该合同本身应属抵押借款合同,属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经向奔驰租赁公司释明,由于其不同意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处置本纠纷,故其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二审法院保持与一审法院基本相同的裁判观点,并驳回上诉。
该案中法院的判决显然对现有该行业当中常见的业务形式作出了否定性评价,而“名租实贷”的观点若受到司法机关的逐渐普遍承认,则将会对汽车融资租赁行业产生重大的影响,进而可能造成整个行业经营上的违法性风险。
二、司法实践中“交易型售后回租”性质认定标准的归纳
在该案中,除了一审将车辆称为“不动产”的明显错误外,该判决的论证依据当中存在较多未展开之处。对此,我们结合近年来的典型案例,对“交易型售后回租”性质的判断标准进行归纳分析。
(一)车辆是否进行转移登记不应成为交易性质判断的基础
1.根据立法规定,车辆所有权的转移不以转移登记为生效要件
《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的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该条款与原《物权法》第二十四条内容一致)。因此,在车辆所有权的转移效力上,仍应以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这已经获得司法机关和理论学说较为统一的认识。因此,该案中法院以车辆所有权未转移为由认为双方之间的融资租赁关系不成立,在论证基础上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2.融资租赁中非典型转移方式的效力应得到承认
有法院认为,在汽车融资租赁交易中,《融资租赁合同》《车辆买卖合同》等文件已足以证明出租人与承租人转让车辆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及转让条件、方式。双方选择占有改定的方式合法有效,未办理转移登记也并非案涉车辆所有权转让的生效要件(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民再309号民事判决书)。此类观点可以表明,对类似“奔驰融资租赁案”中通过占有改定方式进行的所有权变更,并不因未登记而不产生效力。此外,也有法院认为,涉案车辆虽登记在承租人名下,但当承租人出具《所有权确认函》时,可确认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为出租人(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21)沪74民终23号民事判决书)。
由此可见,车辆所有权转移中的交付在形式上并不局限于典型的交付方式,如果能够从双方意思确定转移该车辆所有权的真实意思,也应当承认该种转移的效力。进而,在判断“交易型融资租赁”的性质和效力中,车辆是否办理转移登记也不应成为决定因素。
(二)“交易型售后回租”实质性质的判断核心在于双方真实意思
对于实践中复杂多变的融资租赁形式,现有司法观点开始更多地关注于法律行为背后隐含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应当“注意处理好民商事审判与行政监管的关系,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参见《九民纪要》引言)
对于担保与借贷之间关系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受制于当事人之间签订合同的外观和名称,而应由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和合同的实质内容来决定,只要确认双方当事人就借贷问题达成了合意且出借方已经实际将款项交付给借款方,即可认定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128号民事裁定书)。因此,单独的凭借车辆所有权已转移至出租人的理由,还不能完全确定该类业务的性质。
(三)影响“交易型售后回租”中双方真实意思判断的可能因素
1.购买环节的支付对象可能影响性质的认定
在“售后回租型”融资租赁中,承租人向出租人购买租赁物是认定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有观点认为,融资租赁合同的签订不能完全证明双方间的法律关系,若缺少出租人实际购买租赁物的环节,则难以对双方之间融资租赁关系进行认定(参见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8)辽0402民初681号民事判决书),结合该类案件的背景,其中“实际购买租赁物”环节,应当在于强调双方真实的资金往来与租赁物转移,进而如果(像“奔驰融资租赁案”中)出租人的支付对象不为承租人时,则可能会影响到对该种交易性质的判断。
2.不恰当的登记极易增加司法机关的抵押贷款性质印象
作为特殊动产的车辆,其登记内容是认定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重要标准。有法院即认为:在融资租赁中,若双方向车辆管理部门提交出租人将车辆抵押而非买卖的合同,则双方行为更符合抵押贷款的法律要件(参见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8)辽0402民初681号民事判决书)。这也同“奔驰融资租赁案”中所反应的情况类似。
3.租赁物是否实际交付可能影响到对融资租赁关系的认定
《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从事售后回租业务的金融租赁公司应真实取得相应标的物的所有权。标的物属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其产权转移必须到登记部门进行登记的财产类别的,金融租赁公司应进行相关登记。”
可以推论,租赁物客观存在且所有权由出卖人转移给出租人系融资租赁合同区别于借款合同的重要特征(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286号民事判决书),虚假的租赁物交付将会导致法院产生借贷关系的认识倾向。如有法院认为,如果承租人没有收到租赁物,只是签订了租赁物交接书,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不成立,双方应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参见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2民终1435号民事判决书)。
4.未办理转移登记仍将影响“交易型售后回租”的性质
虽然车辆所有权的转移并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在双方仅签订协议而未进行转移登记的情况下,可能影响到法院对双方真实意思的判断。如有法院认为,融资租赁合同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出租人购买租赁物取得所有权,在车辆始终登记在承租人名下的情况,出租人主张其与承租人之间是售后回租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缺乏依据(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闽民申3888号民事裁定书)。反向角度上,另有法院认为,由于机动车涉及公共安全,国家对机动车管理实行实名登记制度,故保持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的一致性,是机动车所有人正确履行法定义务的必然要求。仅以登记权利人作为认定机动车所有权人的唯一标准虽有不妥,但并不影响融资租赁公司的实际权利(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申782号民事裁定书)。
(四)“交易型售后回租”性质中实质的矛盾
可见,在“交易型售后回租”中存在的主要矛盾点是:车辆转移形式本身的合法性和自由行与综合因素对整体交易形式性质判断的影响。
在“奔驰融资租赁案”所体现的交易形式中,虽然双方达成了车辆购买条款,行为上也符合了车辆所有权转移的客观要件,但是:第一,承租人并未实际向出租人购买该车辆,而是将款项直接支付给车辆的销售方,虽然在法律关系上,车辆的购买方仍为承租人,出租人仅为第三方支付的主体,但显然缺少了出资人直接向承租人购买租赁物的环节;第二,虽然双方签订了《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但出租方并未办理所有权登记。相反,双方签订了《抵押合同》并进行了抵押登记,较明显地体现出了抵押贷款的特征;第三,承租方与出租方虽然签订了《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但支付对象为车辆销售方,且始终并未真实的取得租赁物,这也可能产生对该交易性质的影响。
综上,在“交易型售后回租”的交易形式中,承租方与出租方在购买环节的支付对象、抵押登记的设立、租赁物的交付方式、未办理转移登记等因素,可能综合性地影响到法院双方真实意思的认定,进而最终产生对其融资租赁性质的否定。
三、“交易型售后回租”可能面临的监管限制与法律风险
(一)近期可能受到监管上更为严格的限制
2020年5月26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应当以权属清晰、真实存在且能够产生收益的租赁物为载体……”第八条规定:“融资租赁公司不得有下列业务或活动:……(二)发放或受托发放贷款……”,明确了对融资租赁公司在经营中租赁物产权明晰性和真实性的要求,同时在原则上禁止融资租赁公司发放贷款。
在本暂行办法颁布前后,各地监管机关对“名租实贷”的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2019年12月2日,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开展非持牌住房置业担保公司和车贷担保公司等机构摸底排查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未取得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但实际上经营融资担保业务的汽车消费贷款担保公司等机构进行全面排查。2020年8月12日,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部分融资租赁公司涉嫌违规开展业务的风险提示》,对行业中“以融资租赁业务名义实际从事发放汽车抵押贷款业务”的问题进行了警示。2021年3月9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融资租赁公司汽车融资租赁业务的通知》,要求融资租赁公司不得以车辆售后回租或其他形式变相开展个人抵押贷款业务,不得在业务宣传中使用“以租代购”“汽车信贷”“车抵贷”“车辆贷款”等语义模糊或不属于融资租赁业务经营范围的字样,不得为客户提供或变相提供融资担保服务。2021年2月1日,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上海市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预计在近期也将会对于该行业发布正式的监管办法。
因此,“交易型售后回租”业务在近期可能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限制,若现有经营方式遭到司法普遍性地否认,可能导致监管机构相对应地将该类业务列入禁止经营的范围。
(二)现有经营方式可能触及非法经营罪等罪名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规定,若“交易型售后回租”的经营形式被认定为抵押借贷,由于融资租赁公司通常不具备经营金融借贷的相关资质,即可能会触及非法经营罪以及其他罪名。例如,2019年12月,上海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因“名租实贷”等事件涉嫌诈骗,被立案侦查。
(三)可能面临民事权利的劣后或难以主张
若法院否定“交易型售后回租”的融资租赁性质,将导致出租人对车辆所有权的丧失,产生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问题(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申110号民事裁定书)。在诉讼过程中,若法院将该类业务认定为民间借贷,则应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268号民事裁定书)。然而,出于合规性要求和监管限制,融资租赁公司在司法争议中可能难以主动承认该类交易的抵押贷款性质,最终造成法院对以融资租赁类为案由的起诉予以驳回。
四、“交易型售后回租”业务法律风险的应对建议
虽然现有法律法规中对“交易型售后回租”尚未有针对性规定,但已有司法判例和监管要求表明该类业务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针对现有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应对建议,以供参考:
(一)确认租赁物实际存在并及时办理产权转移手续
融资租赁公司需严把风控,确保租赁物为实际存在之物并及时办理产权转移手续,确保在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租赁物能够实际进行产权转移。
(二)避免抵押登记的设立
在对车辆进行回购过程中,应当避免抵押登记的设立,明确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设立,防止该类经营中抵押贷款影响因素的出现。对暂时无法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情况,也应当首先通过合同确定出租方的所有权。
(三)避免向销售方直接支付融资款项
在经营当中,应确保融资款项向承租人(买受人)的直接支付,避免向汽车销售方直接支付融资款项。在承租人(买受人)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也应考虑采取购买车辆后直租的方式。
(四)确保租赁物的特定化与实际价值的相当
对租赁物难以特定化、实际价值过低等情况,也有法院认为出租人一开始便并无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意愿,进而将该种行为认定为借贷。对此,融资租赁公司应从业务开展的初期即确定特定的租赁物,并保证实际价值与融资金额的相当。
王家骏
法学博士
专长领域:金融保险、公司商事、证券及资本市场
邮箱:jason.wang@sgla.com
中联律师事务所
中联律师事务所 2008 年成立于上海,2020 年成为中世律所联盟发起创办的一体化全国性品牌所,是一家立足国内、面向全球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中联是中世律所联盟在中国首次以联盟做大方式,推动律师行业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的最新成果。中联秉持包容、合作、进取、开放的联盟文化理念,融合各地优秀成员所的丰富资源与荣誉,以高于同业的一体化知识管理体系与执业标准,全新诠释中国最好律所联盟成功发展的精神内核与事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