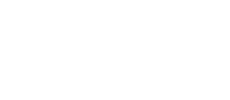2015年4月,事益公司(甲方)与付某(乙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第一条“协议签订的前置条件”第6项约定:甲方融资后,该项目总体投资额1亿元。项目投资和建设期间的经营费用超过1亿元时,追加部分由甲方负责,乙方不追加投资。第二条“乙方投资及收益计算”第1项约定:乙方投资1300万元,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时间(合同签订后3日内汇款300万元,2015年4月22日前余款全部到位)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甲方为乙方开具收据;第3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建设期间内(1年)按实际收益的15%计算分红;建设期满后,年净收益不足3000万元时,按3000万元计算分红,超过3000万元时,按实际净收益计算分红,甲方承诺四年内支付给乙方的收益达到乙方投资额度,实际收益未达到的,用甲方收益弥补并支付给乙方;第5项约定:分红每年一次,12月30日结账,次年1月15日前分红。第四条“违约责任”第4项约定:因甲方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亏损,乙方不承担经济损失,并按约定标准计算投资收益。协议签订后,付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5年4月14日至6月2日分六笔向事益公司转款1300万元。协议履行过程中,付某多次向事益公司监事林某要求支付其固定收益,但是事益公司均未履行。双方发生纠纷,多次协商未果。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投资合作协议》;二、事益公司向付某偿还1300万元借款,支付付某624万元利息(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支付付某律师代理费19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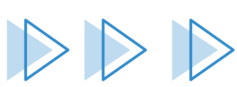
一审法院认为
从《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看,付某的收益是采用固定回报的方式,并且有保底条款,明确了案涉1300万元的性质是借款,而非投资;事益公司经营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付某不承担损失,但无论盈亏都要按照约定标准计算收益,由上述约定可知,付某不参与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投入的资金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所以不难看出事益公司的真实意思是借款;协议的目的是以投资为名,通过股权的份额作为担保,向付某借款。故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实质是民间借贷,而非投资。现按照双方协议约定,事益公司一直迟延履行支付利息的主要债务,付某多次催要,并给予合理期限,但是在合理期限内,事益公司仍然没有履行,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付某依此主张依法解除双方签订协议的诉讼请求有理,予以支持。关于案涉款项及利息给付的问题。事益公司收到付某支付的1300万元后,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按期给付利息,致使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法履行,应依法解除,事益公司应当将案涉借款偿还给付某,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因双方当事人在《投资合作协议》中对诉讼费用(含律师费)的承担做了明确约定,按照约定应由败诉方事益公司承担。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付某与事益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二、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付某本金1300万元;三、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某624万元利息(以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四、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某律师代理费19万元。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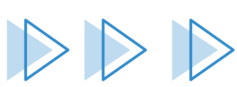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事益公司与付某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内容表明,付某所获收益是以固定回报方式计算,且约定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付某均按标准获得投资收益。因此,《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事益公司工商登记虽变更付某为公司股东,但事益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付某参与了公司的实质性经营活动。付某不参与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投入的资金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该1300万元名为投资,实为借款。仅就事益公司与付某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原审认定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事益公司收到付某支付的1300万元后,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按期给付利息,事益公司应当将借款偿还给付某,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并根据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事益公司应支付的利息标准,亦无不当。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事益公司的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