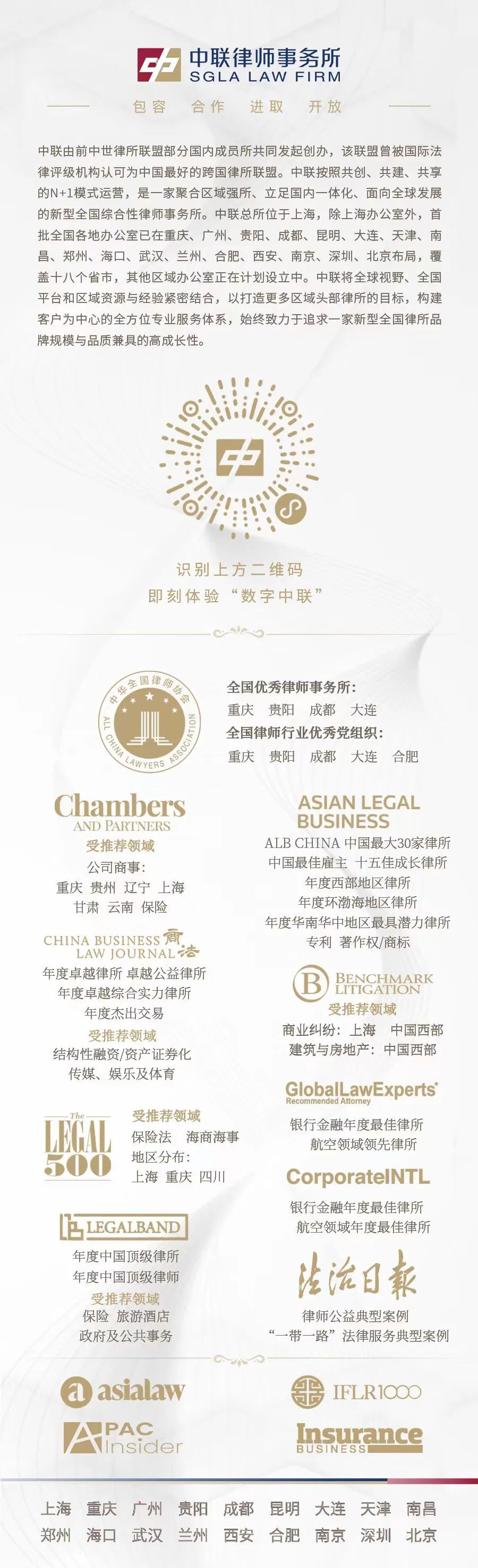前言
南京作为中华民国曾经的首都,留有众多的民国历史建筑。之其中不乏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化遗迹,他们大多被改造为博物馆或纪念馆,供游人参观瞻仰。当然,更多的民国建筑仍旧发挥着居住的基础性作用,成为平常百姓的日常居所。这些民国建筑不同于一般的居住小区,他们往往是独门独户的小洋楼,或是多家人共用的老式弄堂住宅。针对在此类建筑物内发生的产权、居住权以及相邻权纠纷的处理不能等同于其他一般案件,不仅要参考《民法典》、《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基础性法律规定,还要充分考虑是否适用《文物保护法》等特殊类法律的规定。
【关键词】
民国建筑 文物保护单位 邻里关系 赠与合同
【裁判要旨】
案涉建筑系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未划定保护范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现被修改为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文物保护单位”范畴,不能适用该条对建设工程施工的规定。同样,案涉建筑也不适用《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第 4.3.1 条的规定。双方签署的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相关法条】
《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公布)
第五百七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文物保护法》
第二十八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文物保护工程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因特殊情况需要在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前款规定的建设工程或者作业的,必须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前款规定的建设工程或者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案情简介】
南京市某区某小区101室、102室房产左右相邻,均为余氏家的祖产,系早期的民国建筑,被列为南京市某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余氏有2个子女,分别为姐姐余某某1(原告母亲)和弟弟余某某2(被告),两家分别居住于101室和102室,共用屋前屋后两处院落及两个大门。1995年,余氏将101室和102室房屋的产权分别赠与给姐姐余某某1和弟弟余某某2。赠与合同写明:1、不得在房屋中断加盖隔墙;2、两家房屋中的共用墙归属弟弟余某某儿子所有;3、房屋不得变卖。2021年,原告周某从母亲余某某1处受赠了101室不动产的产权。至2022年初,该房屋因年代久远,101室和102室共用的隔墙出现晃动,整个房屋被列为危房,无法继续居住和使用。为实现继续居住的目的,同时获得独立的私人空间,更好的保护双方的个人隐私,在区文旅局、街道及社区相关政府部门见证下,原、被告双方于2022 年 6 月 10 日达成《沟通协议》,约定:1.双方同意前后院子砌筑分隔墙,具体为:(1)后院两扇门之间加砌一道后院墙,高度不超过院内已有的隔墙高度,将后院东西方向一分为二,墙以东院子归被告方所有,墙以西院子归原告方所有,后院大门由原告方维护和通行;(2)前院进出通道处加砌一道后院墙,高度不超过邻马路围墙高度,将前院东西方向一分为二,墙以东院子归被告方所有,墙以西院子归原告方所有,前院大门由被告方维护和通行;(3)前院分隔墙由被告方负责砌筑,后院分隔墙由原告方负责砌筑,前后院的分隔墙由原被告双方共有。2.在前后院子隔墙砌筑完成后,被告方同意原告方对房屋进行修缮、加固等施工,但中间隔墙不能承重,仅可以对公共墙粉饰,涉及中间隔墙的前述施工方案必须征得专业机构或文物部门同意方可施工。3.违约责任: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不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义务的,则被视为违约,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违约方应就守约方产生的直接损失提供完全、有效的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就本赔偿条款进行调查、准备、抗辩所支出的所有费用支出(如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评估费、误工费等)。该协议签字页除当事人签名外,另有区文旅局、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作为见证人签字。沟通协议签订后,原、被告依约砌筑分隔墙。
后被告因擅自在房屋内修建违章建筑,被行政机关强行拆除。被告怀疑是原告举报导致的,故于2023 年 9月雇人将前院分隔墙中间部位砸毁,被毁坏后的墙体破损部位可容人通行。双方就此发生矛盾,原告诉至法院,主张被告将院墙进行恢复,并赔偿相关损失。
【案件焦点】
围绕本案的事实,双方存在以下争议焦点:
1、 因为在长辈的赠与协议中,明确要求原告的母亲不得将房产变卖,双方房屋共用的隔墙归被告之子所有,房屋中间不得加盖隔墙。所以原告母亲将房屋过户给原告以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因违背了上辈的遗嘱而归属于无效?
2、 因为该处房产属于民国建筑,受法律特别保护。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因违背了法律关于文物保护的规定而归属于无效?未经批准,双方是否有权擅自对房屋进行改动?
3、 同样是考虑到对历史建筑和文物在消防安全方面的特别保护,双方擅自修砌前后院墙的行为是否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
4、 被告因违规修缮房屋被认定为违法,继而被行政主管机关强行拆除。那么被告自行拆除院墙的行为是否属于自我纠正违法行为,是否合理?
5、 被告是否因拆除行为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办案思路】
接受当事人委托后,我们律师开展了充分的调研和讨论,就本案争议焦点逐一分析并形成代理意见。
一、针对双方与先辈签订的赠与合同这一问题,我方认为:
1、原告系从母亲余某某1处获赠房屋产权,双方系母女关系,且房屋仍由原告和母亲共同居住至今,所以不存在对外出售房屋或变卖的情况发生,不属于违背了赠与协议的约定。
2、遗嘱的意愿是为了子女更好的生活。现在依据遗嘱办理的继承已经结束,双方获得了房屋的完整产权,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双方对于房屋的处置室深刻贯彻了珍惜物质资源、爱惜民力物力的思想,系维护了标的物的价值,发挥物的效用,以达到保护物的经济价值和效用的目的。双方为更好生活需要,在不侵犯其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上,尤其是与亲属兼隔壁邻居余某某2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修建院墙,并不违背赠与协议的约定,是对法律精神的发扬和遵守,完全合乎法律规定。
二、我国《文物保护法》保护的范围限于特定种类的文物,本案双方的协议并不违反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根据文物法的有关规定,文物保护须经过有权机关登记并公布,具体可分为四个等级: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而本案案涉标的物属于某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属于文物保护法第13条所称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它不属于文物保护法第17条所规定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畴,既然不是强制保护性文物,那么作为居住属性的房屋而言,居住使用的权利归属于产权人。双方自愿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对其建筑施工的要求不能适用该条法律规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况且本案涉及的院墙并非建筑主体工程,而是附属的临时性建筑,并不需要经过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双方所砌的分隔墙已经充分遵循了不改变文物现状的原则,且有助于文物的安全,双方根据自身利用的需要,进行的是合理、可逆性的装修和装饰,并未改变主体结构,构不成对文物的侵犯,亦是遵循法律而为之的行为,该行为亦受法律保护。
三、至于双方修砌前后院墙是否存在消防隐患的问题,我们认为不构成。我国《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第4.3.1条所列的需要两个以上出口的防火要求,是对文物建筑防火保护区的明确要求,而关于“文物建筑防火保护区”的名词解释,该导则的2.0.1条也明确表明是依法划定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而案涉标的物并不属于文物保护单位,更谈不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从而并不适用该导则的要求。另一方面,案涉标的物系居民住宅,个人家用,而非列入运营管理的文物遗迹,人流日常仅限于家庭成员,对于居民住宅的消防要求亦无法达到大流量文物遗迹的标准,不能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配备消防通道和安全设施,更不能不顾产权人的居住需要而人为设置障碍,且案涉标的物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亦根据有关规定向原被告家配备了灭火器等防火设备,该案涉标的物已经达到正常消防安全需要。故而沟通协议砌墙的分割院落的条款并不违法消防的规定,完全符合居民住宅的消防安全标准。所以不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
四、至于被告假借行政机关强行拆除违章搭建的借口雇人违法拆除隔墙的行为,则完全是故意混淆视听,企图欺骗世人。
一方面,在协议签订后,被告因私自在房屋内加盖违法建筑而收到行政机关的处罚,但该处罚本身并不包含隔墙。所以被告故意毁坏院墙并转嫁给行政机关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另外一方面,案涉诉争的分割墙亦不属于违建的范畴;违法建筑本质来讲是妨碍社会公共利益、不符合城乡整体规划、违反了法定的建造程序而形成的建筑;其中妨碍社会公共利益、不符合城乡整体规划为其实质要件,违反了法定的建造程序为其形式要件;只有同时具备实质和形式要件的建筑,并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才能认定其为违法建筑;根据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城乡规划法》第64条规定;国务院于1993年6月发布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37条、建设部1995年6月颁布的《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第40条以及全国各省、各直辖市根据法律制定的地方法规都作了相类似的规定。从上述法律法规看,未依法申办建筑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工程许可手续建筑是一种“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建筑,实践中人们习惯称之为“待确权建筑”。因此,形式要件不是违法建筑的独立构成要件,仅具备了违法建筑形式要件建筑,还不能径直认定其为违法建筑。具体到本案,被告与原告就沟通协议所约定的分割砌墙,为自家院落装饰性,可逆性建筑,且未超过原有墙体本身高度,并无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犯可能,且未违反城乡整体规划,反倒是促进、改善,调和邻里关系的合规建筑,是减轻政府基层部门调解邻里关系的压力;避免政府行政资源的浪费,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同时,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确认是认定违法建筑性质的必经程序,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确定为违法建筑前,不是违法建筑;案涉的相关执法部门并未作出对案涉建筑物的违法性作出定论,理应认定建筑不具备违法性,也即案涉沟通协议具备相应的合法性。
五、至于被告是否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1、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晰的看到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执行。被告擅自砸毁院墙的行为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被告理应按照约定承担一切赔偿责任;2、另一方面,如果双方没有损害赔偿的约定,那么被告的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侵权行为,应当按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相关内容执行,被告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评析】
本案的关键是案涉房屋性质的认定以及双方加盖的院墙是否属于违章建筑。律师承办本案后,充分考虑案涉房屋的民国建筑性质以及邻里纠纷处理的难度,做了大量的调查了解工作,包括向区街道、文保局、市容城管等部门多方走访。在彻底查清案涉房屋根本属性的基础上,果断分析论证出不能机械的套用文物保护法的一般性规定来审理本案,继而得出双方修建院墙的合同合法有效,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所谓的消防安全隐患。本市某区法院在充分听取律师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决,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并限期修复院墙。在一审判决后,被告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后判决维持一审的判决结果。至此,本案审理才全部归于终结。

编辑 | 张军 王家豪
审核 | 张军
作者简介
往期推荐
 中联动态 | 王云霞律师为区属国企开展国企董监高人员的合规履职与风险防范讲座
中联动态 | 王云霞律师为区属国企开展国企董监高人员的合规履职与风险防范讲座
 中联动态|王哲禺律师应邀在“信·数据π——客商风险管理”沙龙中做《新公司法视野下应收账款催收》主题讲座
中联动态|王哲禺律师应邀在“信·数据π——客商风险管理”沙龙中做《新公司法视野下应收账款催收》主题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