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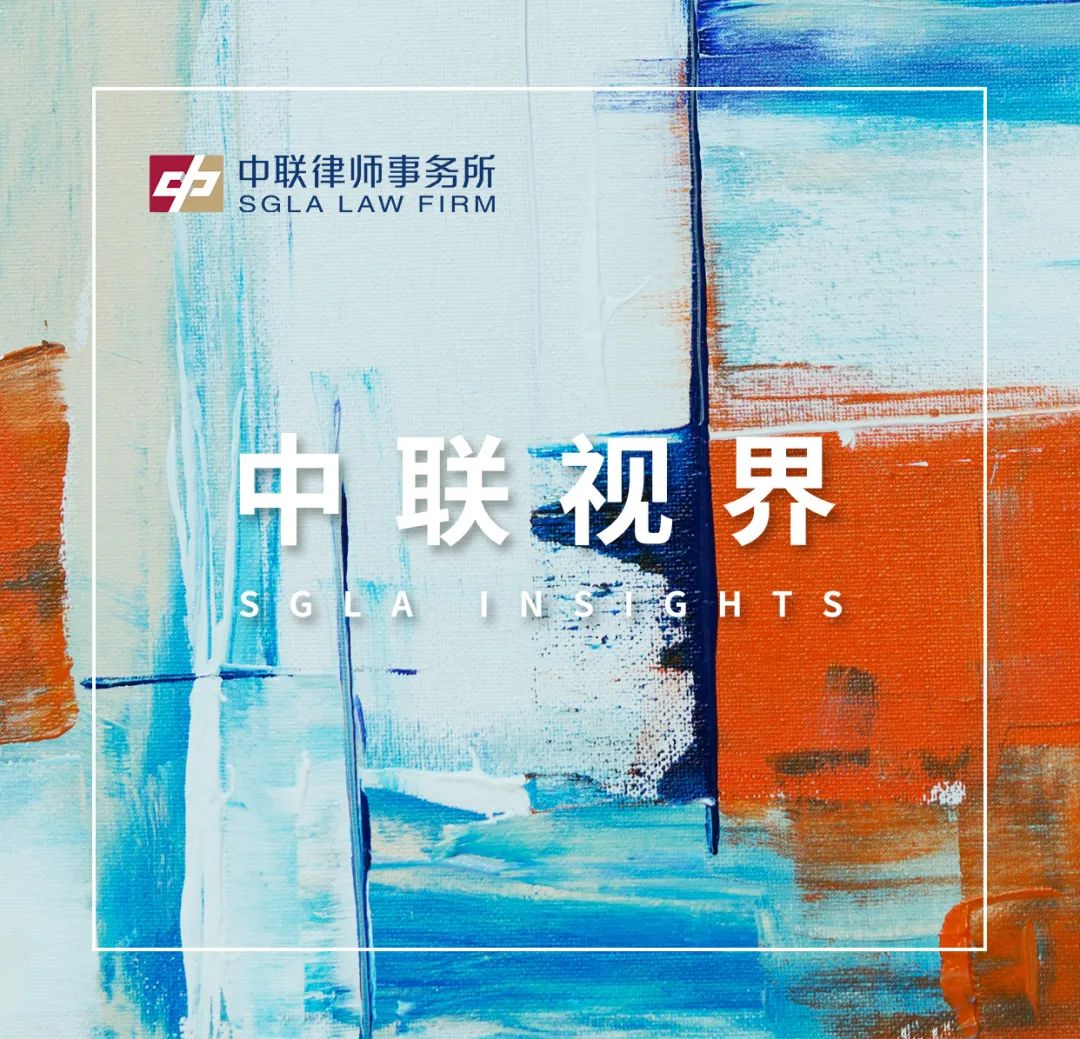
一、案情简介
本所丁钰律师团队系本案二审阶段上诉人的代理人。被上诉人一某公安分局于2024年1月16日作出〔2024〕xx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强戒决定”),认定上诉人系“吸毒成瘾人员”,且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以下简称《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上诉人作出强制隔离戒毒二年(自2024年1月16日至2026年1月15日)的行政强制措施。上述强戒决定作出后,上诉人被送往某女子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
上诉人对此不服并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被上诉人二某区人民政府于2024年4月23日作出〔2024〕第xx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强戒决定。上诉人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撤销被诉强戒决定及复议决定。一审法院于2024年8月29日作出一审行政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结合当事人陈述及本案行政复议及一审阶段材料,我们发现,本案起源是:上诉人无吸毒史,但在2021年10月某天在酒吧未设防备地吸食了一名偶遇的陌生男子递来的电子烟(有且仅有一次);上诉人当晚返回家中休息,第二天便有某公安分局民警登门检查,将上诉人带去进行尿检和毛发检测,检测结果呈弱阳性,上诉人事后才意识到可能是接触了含毒“电子烟”。结合案件材料,当时上诉人未有吸毒成瘾戒断反应,但仍被“鉴定”为“吸毒成瘾”,上诉人申辩自己并未吸毒也不知为何体内会检测出毒品成分,执法单位对其申辩不予采纳,并对其作出拘留十日的行政拘留决定。基于当时上诉人对此事的轻量化错误认知,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未提起行政诉讼。
前述行政拘留结束后,社区戒毒工作部门与上诉人签订戒毒协议,要求上诉人进行社区戒毒。自2021年10月15日起,上诉人在社区戒毒期间已配合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吸毒检测十多次,检查结果均为阴性。而某公安分局之所以作出本案被诉强戒决定,并非因上诉人在社区戒毒期间吸毒,而是因为其在社区戒毒协议履行期内因工作原因离开住所地并出国、出境,违反了协议中规定的人员管理报告制度,但在被诉强戒决定中仍认定上诉人为“吸毒成瘾人员”。我们认为,本案在客观事实上,上诉人从未主观故意“接触毒品”,更不应被认定为“吸毒成瘾人员”,而强制隔离戒毒的措施客观上将限制上诉人的人身自由两年,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在作出决定前应当保持高度审慎态度。
二、本案争议焦点
1、公安机关在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前,是否有义务认定行政相对人系“吸毒成瘾人员”?
2、如公安机关有义务认定相对人系“吸毒成瘾人员”,可否直接以其他公安机关在先的“吸毒成瘾报告”为依据?
3、如以其他公安机关在先的吸毒成瘾报告为依据,在后的公安机关是否可以再次进行认定?何种情况下,必须再次进行认定?
三、二审阶段核心代理意见
(一)被上诉人一对上诉人的毛发、尿液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检测的鉴定结论显示,上诉人体内不含有毒品,故上诉人并非“吸毒人员”,且其自社区戒毒以来的历次检测均为阴性,足以证明其不具有成瘾性,更非“吸毒成瘾人员”
2024年1月15日,被上诉人一委托某检验技术有限公司对上诉人的毛发和尿液进行检测,相关《鉴定意见书》明确:“所送头发总长约5.5㎝,其中距根部3㎝段未检出成分”;“所送尿液未检出”。这说明,2024年1月15日之前的六个月内,上诉人不含毒品成分、不存在吸毒行为。
此外,被上诉人一已查证:2022年12月之前上诉人积极配合十余次检查且均为阴性;2022年12月份以后,上诉人虽未在社区戒毒执行地检测,但在广州等地出差时,亦积极配合当地相关部门,检测结果仍为阴性,足以证明上诉人对毒品不具有成瘾性。
《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吸毒人员同时具备以下情形的,公安机关认定其吸毒成瘾:(一)经血液、尿液和唾液等人体生物样本检测证明其体内含有毒品成分;(二)有证据证明其有使用毒品行为;(三)有戒断症状或者有证据证明吸毒史,包括曾经因使用毒品被公安机关查处、曾经进行自愿戒毒、人体毛发样品检测出毒品成分等情形。” 显然,上诉人不符合该办法中“吸毒成瘾人员”认定要件,也即上诉人不属于“吸毒成瘾人员”。并且,在被诉强戒决定作出前的调查期间,被上诉人一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社区戒毒期间有新的接触毒品事实,故其将上诉人认定为“吸毒成瘾人员”,属于明显认定事实错误。
(二)上诉人违反社区戒毒协议仅能证明其未遵守协议规定,不能证明其系“吸毒成瘾人员”
上诉人在2023年期间确有未遵守《社区戒毒协议书》中要求的定期报告、检测等规定的行为,但并不致被作出强制隔离戒毒这一限制人身自由两年的严重行政强制措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据此,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的法定要件首先是认定构成“吸毒成瘾”,如非“吸毒成瘾人员”,即使未能依约进行定期报告、检测,仍不构成该条所规定的强制隔离戒毒情形。同时,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系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法》第十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第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因此,不可仅因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约定便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协议亦不得约定“违反本协议将被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等此类违约责任,否则应属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被上诉人一仅以上诉人违反社区戒毒协议为由,对非“吸毒成瘾人员”的上诉人作出被诉强戒决定明显违法。
(三)被上诉人一在作出本案强戒决定时,有义务重新进行“吸毒成瘾”鉴定而未鉴定,错误地将在先作出行政拘留决定的公安机关提供的“吸毒成瘾认定报告”直接作为被诉强戒决定作出时上诉人是否“吸毒成瘾”的认定依据,其事实认定错误
其一,本案中自始至终仅有一份形成于2021年的“吸毒成瘾认定报告”,而该报告是在先作出拘留决定的公安分局于2021年责令上诉人接受社区戒毒这一行政行为的依据。然而,本案被诉强戒决定与前述拘留决定系两个不同的行政行为,被上诉人一不能直接采纳其他行政机关作出在先前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事实认定报告,而应当对上诉人重新作出是否系“吸毒成瘾人员”的认定。被上诉人一对此理应明确知悉,然而其提供的证据中均无对上诉人是否构成“吸毒成瘾”的最新认定材料。
其二,如前所述,上诉人自社区戒毒以来的十多次检测均为阴性,足以证明其不具有成瘾性。在相关基础事实与“吸毒成瘾”存在根本违背的情况下,认定其为“吸毒成瘾人员”是背离常识的,被上诉人一应当秉持实事求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重新鉴定并确认上诉人是否为吸毒成瘾人员,以避免损害当事人基本权利。
其三,根据当地市场监管部门2023年发布的《医疗机构吸毒成瘾认定服务规范》的规定,《吸毒成瘾认定报告》应当是由医生、护士、辅助人员共同认定,并由2名吸毒成瘾认定医生签发。而本案在先的2021年“吸毒成瘾认定报告”仅有一名认定人,该认定报告已经不符合本案被诉强戒决定作出时的规范要求,被上诉人一应当以作出强戒时的吸毒成瘾认定标准为依据,再次委托鉴定。
其四,本案上诉人与其他存在复吸或有多次吸毒史、明显戒断反应的人员明显具有根本区别,当在案全部证据高度指向上诉人不是吸毒成瘾人员时,行政机关应当再次作出成瘾鉴定,以充分、审慎地确定是否作出强戒决定。
因此,被上诉人一坚持仅依据在先作出行政拘留决定的公安机关于2021年作出的“吸毒成瘾认定报告”,即认定上诉人在2024年系吸毒成瘾人员,显然事实认定错误。根据《禁毒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一作出被诉强戒决定前应当先认定上诉人是否为“吸毒成瘾人员”,但其并未依法履职。
(四)关于本案被上诉人一有必要重新作出“吸毒成瘾”鉴定的进一步探讨
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坚持认为社区戒毒以及强戒决定是一个递进过程,只要有首次的成瘾鉴定即可,无需再次鉴定。然而,本团队认为,被上诉人一的这一理解应具备至少两个前提:1、首次成瘾鉴定以及社区戒毒决定合法有效;2、首次成瘾鉴定的有效期至少有三年。显然,该两个前提未必在每个案件中都必然成立。也正因此,《禁毒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是“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而不是“签订社区戒毒协议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立法采取的严谨措辞更表明作出强戒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始终秉持高度谨慎态度。
正如前文所言,本案中的全部证据均高度指向上诉人不是“吸毒成瘾人员”,对本案这类特殊情形再次作出成瘾认定,不损害包括公众在内的任何人利益,反而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避免错案。可以说,本案的出现有助于公安机关在禁毒领域完善执法逻辑。如被上诉人一坚持认为在任何情形下均无需再次作出成瘾鉴定,根据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对同一法条有不同理解时选择对相对人不利的解释,需要被上诉人一提供合法性依据并承担证明成本。
(五)本案行政执法活动存在的其他程序问题
本案中,被上诉人一未对上诉人的陈述、申辩内容予以充分核查,对于上诉人与案涉社工的调查笔录的多处矛盾内容未进行核实调查,径行采纳社工的陈述,事实调查不清,程序违法,严重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八条之规定:“询问违法嫌疑人时,应当听取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对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应当核查。”
四、案件的实质化解效果
结合代理人在本案中已经充分发表的代理意见,经与被上诉人及二审主审法官的多次深入沟通,在法院协调下,被上诉人一变更了强制戒毒措施,当事人得以在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从女子戒毒所走出,与家人团聚。至此,当事人已经在女子戒毒所被“强制隔离戒毒”一年有余。本所丁钰律师团队作为本案二审代理人,在办理本案的过程中深感与相关执法机关的沟通难度大、阻碍多,但本着耐心、细心和心中对案件本质公正的把握,仍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亦获得了客户的高度信任与肯定。
五、后记
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依然是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安全的全民公敌,如此大体量的禁毒工作有赖于以公安机关为主的常抓不懈,我们之所以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社会,得益于国家对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零容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殷切希望相关执法部门以本案为鉴,进一步完善禁毒工作的行政执法程序,不断完善执法规范,避免此类“误伤”再次发生。
丁钰
高级合伙人
专业领域:合规与政府监管;争议解决;公司商事。
邮箱:magnolia.ding@sgla.com
张文婷
律师
专业领域:合规与政府监管;争议解决。
邮箱:wenting.zhang@sgla.com
申昱菲
律师
专业领域:合规与政府监管;争议解决;城市更新与房地产
邮箱:yufei.shen@sgl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