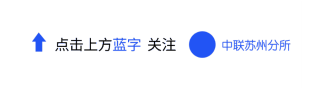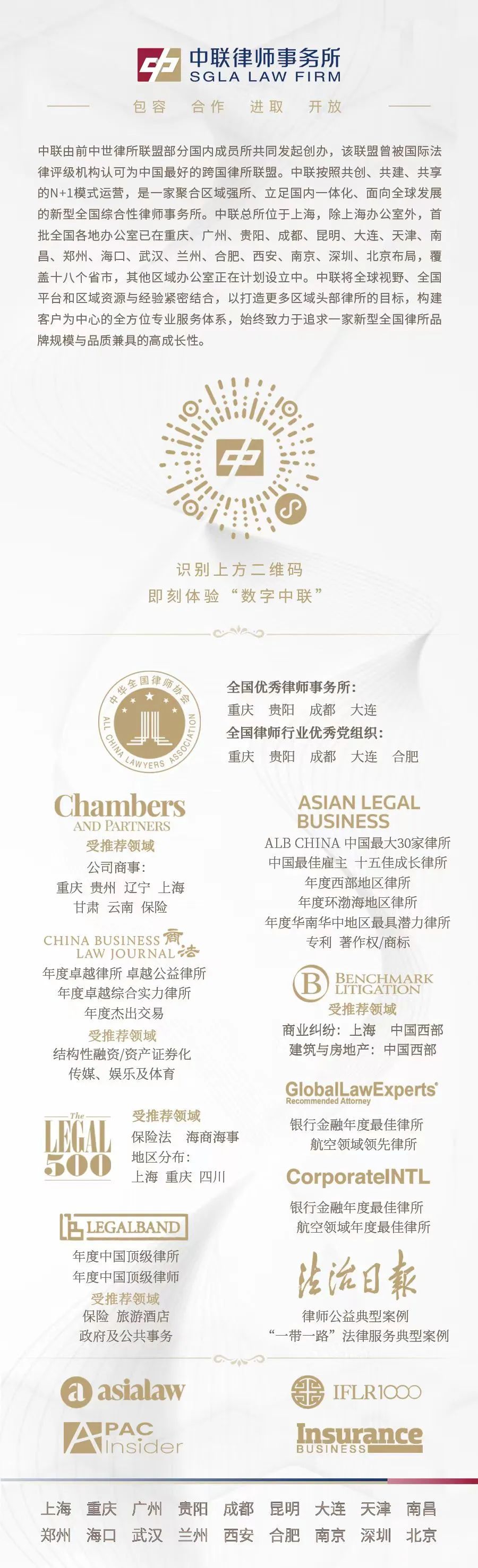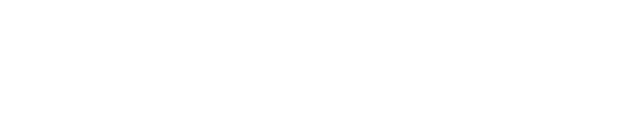
裁判要旨:
公司成立后,股东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变更出资方式。但在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已被法院裁定执行终本的情况下,将出资方式由认缴货币出资变更为知识产权出资,具有逃避货币出资故意的,属于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当认定该变更行为不对债权人发生法律效力,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仍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1
案 情 简 介
某商贸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实际经营投资业务,成立时股东许某甲、许某乙分别认缴出资98万元、2万元,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48年5月6日,出资方式为货币。因公司与王某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2023年1月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某商贸公司向王某支付投资款、律师费共计35万余元。之后,王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认定某商贸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于2023年3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后王某申请追加许某甲、许某乙为被执行人,法院裁定驳回王某的请求,王某不服该裁定,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经查,2023年4月19日,许某甲、许某乙受让“一种打包模块及其中药自动配药系统”的实用新型专利。次日,某资产评估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载明该专利技术市场价值为100万元。同日,某商贸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确定许某甲、许某乙的出资方式变更为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出资,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确认已收到许某甲、许某乙缴纳的实收资本100万元。2023年6月20日,上述某资产评估公司注销登记。许某甲、许某乙在本案中据此主张已经完成出资,不应对公司债务再行承担责任。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债权人对公司公示信息享有信赖利益,股东在公司债务对外不能清偿的情况下,将货币出资变更为非货币的知识产权出资,降低了财产的流动性,逃避货币出资义务,主观上有逃废债务的恶意,客观上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构成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该变更出资行为不能对抗债权人王某对某商贸公司在先的债权,不产生出资的法律效力。因某商贸公司目前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具备破产原因,遂判决许某甲、许某乙在各自未出资范围内对某商贸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对王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2
律 师 评 述
于公司法人而言,股东的出资系法人财产独立的直接来源和基础,股东出资数额、期限、方式的明晰与否直接影响着公司根基稳定性。《公司法》第四十六条和九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上述事项。《公司法》第六十六条更是将上述事项作为“重大事项”设置了更高的表决通过标准。
实务当中,对于股东变更出资方式的认定,除履行法定和章程规定程序外,还应兼顾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债权人的利益。本案中,某商贸公司处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特定情形下,尚未实缴出资的股东能否主张变更出资履行方式?
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条“企业应当自下列信息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和《公司法》第四十条“公司应当按照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下列事项:(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的规定,股东出资数额、比例、方式等事项均为公司需要对外公示的重要内容,因为其变化会对公司现实或潜在的债权人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于非货币出资,尤其是知识产权出资,相比货币出资,其清偿能力及流动性明显受限,存在着无法变现的风险。因此,在公司在债务发生后认缴期限届满之前,以股东会决议方式变更出资方式,是否对债权人有约束力的问题,笔者检索到的相关案例大多数给出了否定的回应。
除本案外,(2024)京03民终11534号案件中,法院作出同本案类似的裁判观点:…在公司正常经营的状态下,股东和公司均未被债权人起诉,此时变更出资方式涉及的仅为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但当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权,股东变更出资方式便可能会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允许股东不受限制地变更出资方式,将认缴的货币出资变更为不易变现的知识产权等非货币出资,无疑会损害债权人通过股东出资实现其债权的期待利益,影响债权的受偿。因此,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应当对股东变更出资方式加以限制。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黔民申3922号裁判中,裁判结论亦是如此。在(2024)京02民终13842号判决中,法院作出裁判“...通过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表明自己已完成实缴出资义务。第一,该出资方式与宁某甲公司经工商备案的章程约定的货币出资方式不同。在公司债务产生后,股东将出资方式由货币变更为知识产权要依法经过股东会决议、评估作价、权利转移等法定程序,否则不产生变更出资方式的法律后果,亦不能对抗已经形成的债权;第二,对于首某公司对其验资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中存在的质疑之处,吴某波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亦未申请重新评估,可认定该评估结论不具有可靠性”。可见法院虽并未直接否定公司负债后变更出资方式的行为效力,但通过设置严格的约束和评判条件予以变相否定,也体现了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特定情形下,对股东变更出资方式的约束与限制。
综上,如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下,股东将出资方式由货币变更为非货币,即使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作出股东会决议,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该变更行为不对债权人发生法律效力,从而被认定为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仍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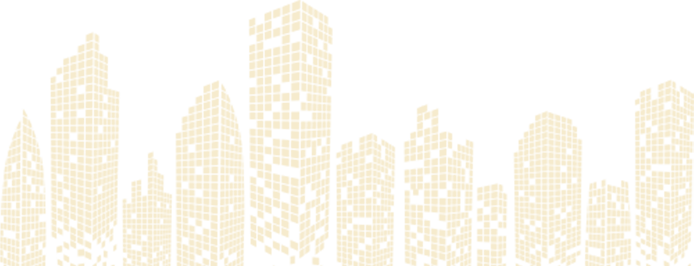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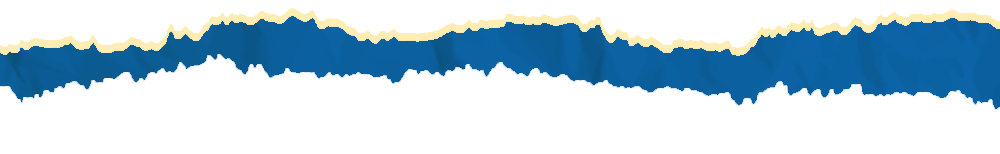
22
作 者 简 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