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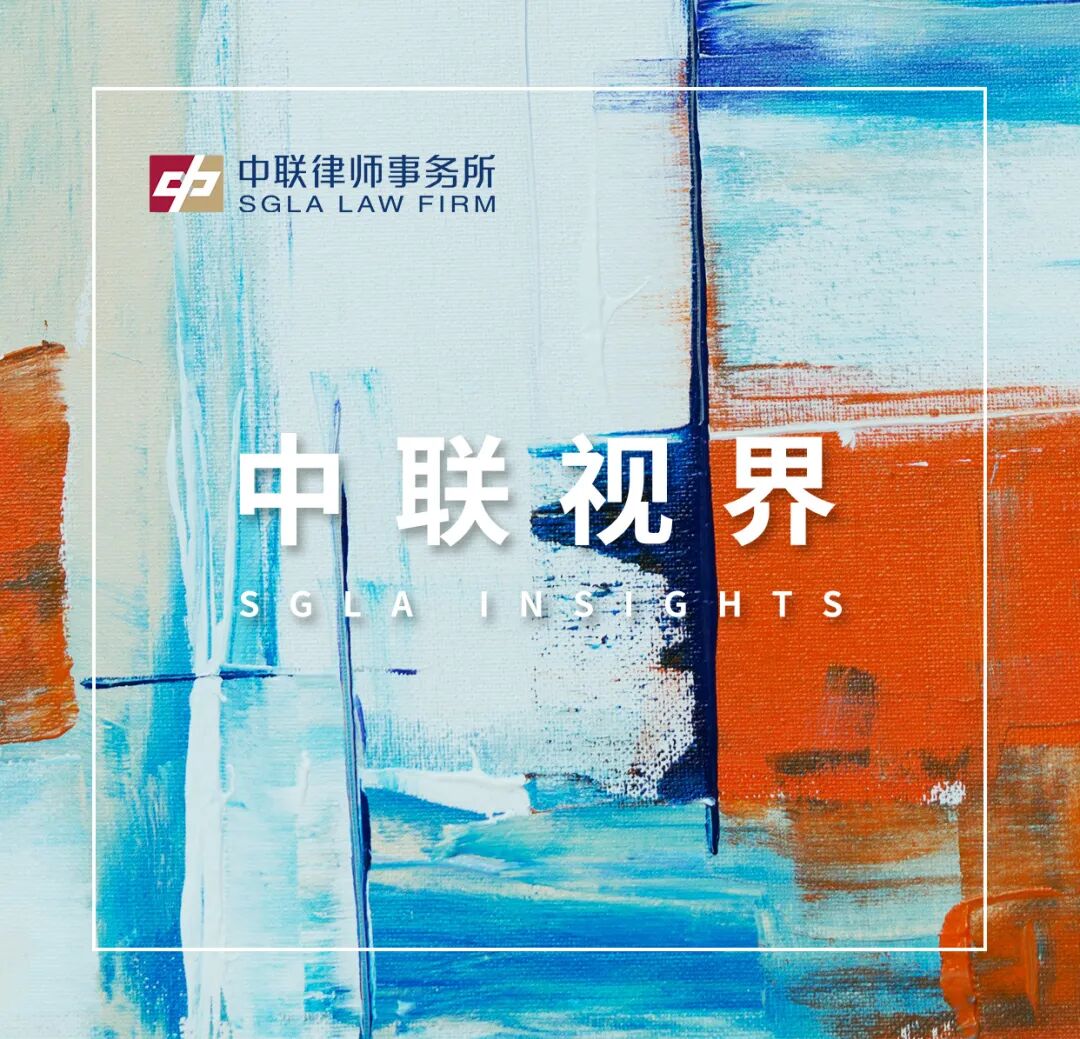
内容摘要
根据宪法性法律规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适用《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基金行业协会对《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梳理,不构成法律解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依法具有履行信息披露、召集私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参与关联刑事案件的职责。
关键词:
法律授权行为、法制统一原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否适用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证券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的问题,在立法部门、监管部门、从业人员甚至包括一些专业的法律人士,各自表现出对法律授权行为的不同理解。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
1
《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规定,公开或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2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维护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竞争秩序,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健康发展,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第二条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在本办法中简称为“基金”。
3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总则部分对适用范围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仅适用于证券投资基金,不适用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笔者从法律适用的宪法性角度,与主流观点持不同意见。
一、《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效力来源
《证券基金法》第十一条 授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依法对证券投资基金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一条 规定,明确《证券基金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其法律依据,即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基金法》对私募投资基金进行监督管理。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般是指《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 所称的“创业投资基金”。
经查证,《证券基金法》属于法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属于部门规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九十八条 、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作为部门规章《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不得同作为法律的《证券基金法》相抵触。
所以,笔者有理由认为不仅不能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排除《证券基金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适用;而且根据《证券基金法》对《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授权,《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未尽事宜应当适用《证券基金法》的规定。
如果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不适用《证券基金法》的判断成立,则当然可以认为中国证监会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督管理没有法律授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活动也无法处于行政监管之下。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无权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立法法》第九十一条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三条第二款都明确规定了“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是中国证监会的部门规章,其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证券基金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事项。执行《证券基金法》的事项,依法不具有否定《证券基金法》实施的法律效力。
(一)“合同约定”无权免除法定职责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的信息披露义务由托管合同约定,没有签订单独托管协议的,托管权利义务内容体现在基金合同中。基金合同可以约定,如基金管理人没有按照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托管人不承担责任。
笔者认为,《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如实向投资者披露基金投资、资产负债、投资收益分配、基金承担的费用和业绩报酬、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情况以及可能影响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其他重大信息”,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一条、《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不得免除和对抗其所执行的《证券基金法》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法定职责的规定。
所以,以《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合同义务,不能作为免除和对抗《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执行的《证券基金法》规定的私募基金托管人法定职责的法律依据。
(二)“未作出规定”无权对抗上位法律
目前的主流观点还认为,基于《证券投资基金法》不适用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托管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义务未作出规定,具体召集义务应当依据基金合同约定。
承前所述,《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的法定职责未作出规定,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一条、《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不得排除和对抗其所执行的《证券基金法》规定的私募基金托管人法定职责,不能得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义务具体召集义务应当依据基金合同约定”的结论。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托管适用《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
根据《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三条第一款 规定,制定《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需要“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的法定职责未作出规定,不仅不能得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义务具体召集义务应当依据基金合同约定”的结论,而且根据《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确立并适用于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百一十六条的“法制统一原则”,可以推导出以下结论:
1
中国证监会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行政监管,属于法律授权行为,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中国证监会无权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行政监管。《证券基金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授权中国证监会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行政监管的法律和行政法规。
2
中国证监会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行政监管,是执行《证券基金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事项,鉴于《立法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的规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客观上没有对抗《证券基金法》的效力,且内容上也没有对抗《证券基金法》的事实,所以中国证监会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行政监管,在《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的法定职责未作出规定的情况下,适用《证券基金法》的规定。
3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照《证券投资基金法》、本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定,对私募基金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被申请人以《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排斥和对抗《证券基金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督管理的适用,明显自相矛盾。
4
所有执行《证券基金法》的事项,统一于《证券基金法》;所有执行《证券基金法》的事项,基于《证券基金法》具有统一性。
5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作为执行《证券基金法》的事项,根据《立法法》的“法制统一原则”,在《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同样作为执行《证券基金法》的事项中未作出规定的情况,基于“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同一性和执行《证券基金法》的统一性,具有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督管理过程中对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适用性。
6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作为执行《证券基金法》的事项,《证券基金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设立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担任基金托管人的行政许可,根据《证券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管理办法》获得的基金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展基金托管业务,理所当然也要遵守继承了《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管理办法》的《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否则就是在破坏《证券基金法》的实施。
综上所述,中国证监会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行政监管属于法律授权行为,不是中国证监会根据自己制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决定自己想管什么就能管什么、不想管什么就能不管什么,而是根据《证券基金法》的授权决定了中国证监会能管什么、要管什么。
笔者有理由认为,法律授权中国证监会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行政监管,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只让你当家,没让你做主。
四、《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解释权属于中国证监会
(一)基金行业协会不是解释规章的适格主体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未禁止同一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不同类别的私募基金。根据《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十三)》,基金业协会在2017年3月底前,未禁止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为多类业务类型的管理人、兼营多类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向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2017年3月31日,基金业协会发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十三)》,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只可备案与本机构已登记业务类型相符的私募基金,不可管理与本机构已登记业务类型不符的私募基金;同一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可兼营多种类型的私募基金管理业务,已登记多类业务类型、兼营多类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需按前述要求进行整改。对已备案且正在运作的存量私募基金,若存在基金类型与管理人业务类型不符情形的,在基金合同到期前仍可以继续投资运作。
但根据《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解释权属于中国证监会;根据《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三十三条第四款规定,中国证监会对《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解释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具有同等效力。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行业协会”)对《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没有解释权,基金行业协会发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十三)》不具有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同等效力,也无权设定增加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义务的规范。
(二)基金行业协会的职责源于法律授权
《证券基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规定了基金行业协会的职责,是法定职责。《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 、第七条第一款 、第八条第一款既没有设定基金行业协会职责的法律地位,事实上也没有设定基金行业协会的职责,而是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属于执行《证券基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的事项。
(三)基金行业协会对规章的梳理不产生新的法律效力
基金行业协会并不因为《证券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产生对《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进行解释的权力。
基金行业协会自2015年开始发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常见问题解答》,在编号为“中基协字〔2015〕103号”的《关于发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常见问题解答的通知》中明确表示,《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常见问题解答》的法律性质是“梳理行业关注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以对外问答形式及时发布。”
基金行业协会自认发布“私募基金管理人在申请登记时,应当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等机构类型,以及与机构类型关联对应的业务类型中,仅选择一类机构类型及业务类型进行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只可备案与本机构已登记业务类型相符的私募基金,不可管理与本机构已登记业务类型不符的私募基金;同一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可兼营多种类型的私募基金管理业务。”所依据的是《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是对“行业关注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的梳理,而不是对《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
同时从立法法的角度,《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没有理由因为基金行业协会的“梳理”发生内容上的变化,所以“私募基金管理人只可备案与本机构已登记业务类型相符的私募基金,不可管理与本机构已登记业务类型不符的私募基金”并不始于《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十三)》发布之日,而始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发布之日。
五、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的法定职责
根据前述宪法性问题的分歧,进一步探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的法定职责。
(一)召集私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职责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基于《证券投资基金法》不适用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托管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义务未作出规定,具体召集义务应当依据基金合同约定。
基于下列事实,笔者持不同观点:
1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作为执行《证券基金法》的事项;
2
执行《证券基金法》的事项遵循法制统一原则;
3
同样作为执行《证券基金法》事项的《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同时具备“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同一性。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的托管人,根据《证券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依法具有“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职责,不受《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尚未规定的限制,也不受《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基金合同义务约定的制约。
笔者有理由认为,基金托管人的法定职责就和人的性别一样,不可以用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改变。
(二)参与关联刑事案件的职责
目前的主流观点同样认为,基于《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不适用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基金合同均未规定私募基金托管人具有代表私募基金委托人参与相关刑事诉讼的义务。
同理,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作为基金托管人的规范,应当以参与关联刑事案件的方式履行《证券基金法》第三十六条第十一项 规定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职责”。
根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规模,当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活动成为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犯罪手段,明显属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八条规定的“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利益受损人数众多、可能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明显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属于“严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或者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
显而易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关联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刑事诉讼,明显符合妥善处理“对发生严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或者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的处理预案要求。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的突发事件处理预案
目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制定的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制度,一般包含《私募基金舆情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私募托管风控管理工作细则》两个方面。
一方面,大部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制定的《私募基金舆情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对应的是托管人自身风险,而不是“严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或者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可谓驴唇不对马嘴。
另一方面,大部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制定的《私募托管风控管理工作细则》的“私募管理人分类管理”不涉及投资人利益内容、“投资人信访维权处置管理”和“仲裁诉讼处置管理”只涉及托管人自身利益,与妥善处理“对发生严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或者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的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制度,是风马牛不相及。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针对自身利益制定的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制度,不属于对“发生严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或者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却可以得到监管部门的支持,足以反映出对法律授权行为的不同理解。
六、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
1
根据《立法法》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适用《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
2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十三)》是对《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的梳理,而不是对《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
3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根据上述法律规范,具有履行信息披露、召集私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参与关联刑事案件的义务;
4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目前针对自身利益制定的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制度,不能应对“发生严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或者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
笔者有理由认为,本文观点更加符合立法部门对上述法律授权行为的理解。

